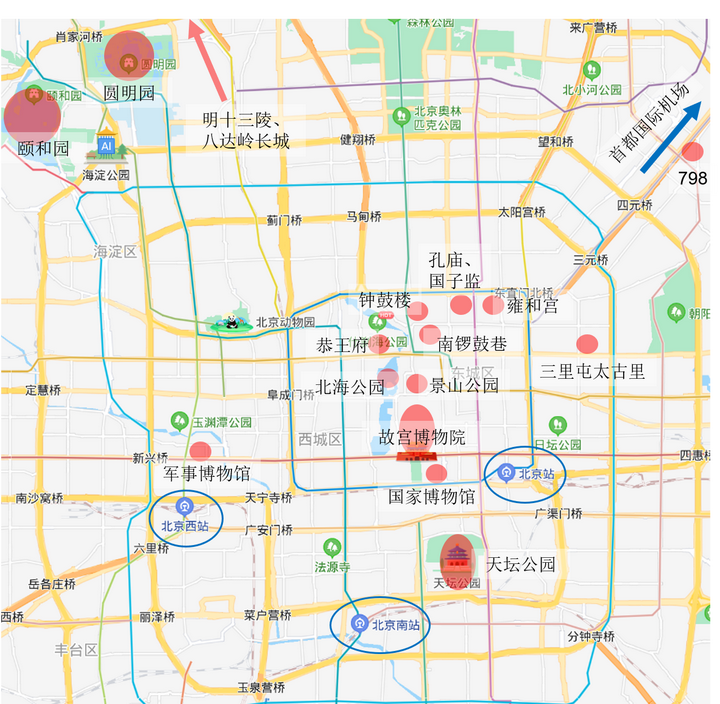“不惑”的一束光
2025-05-20 06:44:00 实时讯息



乍一看书名“活出想要的人生”,第一感觉这本书似乎有“心灵鸡汤”之嫌。但当我读完全书后,却发现书中的44篇作品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芒,刻下了一个时代最真切的光影和精神图谱,足以照亮每一名读者。
1984年,是作家红孩从事文学创作的元年,也是他人生答卷的起始时间,距本书出版整整40周年。可以想象,当他不得已就读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与动物打交道时,他对前途的那份迷茫和无助。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文学这条出路。他开始疯狂地写作,文学给他的生活注入了全新的叙事激情,也赐予他奔放的热情、温馨的诗性和坚定的意志,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生命射去了一束光,照亮他踽踽前行的脚步。写着写着,命运终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
从写作伊始,红孩就试图用自己的文字雕刻出时代巨像和众生百态,挖掘出潜藏其间的时代精神。在离开农场后,这份“野心”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急于求成,往往从身边的凡人琐事和一草一木着眼,通过细致入微的洞察体验,寻求生命的奥秘,探究精神的归宿。无论是第一记中描绘亲人形象的《母亲的挂历》《父亲的“大了”人生》《风居住的街道》,还是第二、三记中把个人发展与城乡巨变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文学初恋》《文学的春天》《今夜,我为你梳头》,尽皆如此。
多年来,红孩一直提倡“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他也用一篇篇力作践行着这个论断。书中44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字里行间“我”的痕迹十分明显,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既包含了人生的磨难和困惑,也包含了本人的解答和应对。这些经历,既是红孩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很容易获得群体性共鸣。读着读着,悄然完成了光的传递,实现了由“我”到“我们”的过渡。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寻根文学等思潮的兴起,使得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新的张扬,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思想资源。进入21世纪以来,广大作家更加注重从价值导向、道德伦理、美学观念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认知和解读,并把成果运用到文本创作中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红孩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活出想要的人生》的后两记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光看标题“生死之间,你为什么不悲伤”和“人生旅途,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就透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终极关怀。红孩没有简单地就经历谈经历,而是注重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看待理想、看待父母、看待老师、看待朋友、看待家庭,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在《日日相忆何处忆》中,当“我”看到许多衣着褴褛、满脸皱纹的老人烧香祷告时,内心燃起一股同情与怜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面对灾难与疾病仅有的一点权利。在《苏武的节杖》中,“我”把两千多年前苏武出使匈奴的节杖与自己爬山的藤杖和母亲的金属拐杖放在一起对照,忽然间领悟了苏武手上那根节杖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发出感慨:“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就不能唤一声苏武大哥呢?”读这两段话时,我禁不住潸然泪下。
红孩的写作已经步入“不惑”之年,这并非某个人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不惑。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不惑只是40年生命的历程,而写作的“不惑”却是在见多识广与饱经沧桑的基础上,将丰满厚实的生命积淀释放出来,充满情感的温度,达到了觉悟人生的境界。这些“不惑”的文字,对于恰好年届不惑的我而言,也正是一束宝贵的光。

《活出想要的人生》,红 孩 著,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4年出版
ELECTROLUX空调全国维修服务号码实时反馈-今-日-汇-总(ELECTROLUX空调空调显示E6故障码,怎么处理? )

三菱电机空调/全国各市服务热线号码实时反馈-今-日-资-讯(三菱电机空调空调线怎么接 )

现代空调服务号码24小时(今日更新)实时反馈-今-日-资-讯(现代空调空调显示h5 )

sacon空调全国(24小时)各售后受理客服中心(sacon空调性价比高的空调 )

COLMO中央空调售后维修号码-人工售后号码实时反馈全+境+到+达(COLMO中央空调空调 h6 )

锦山中央空调售后服务热线号码-全国各售后号码实时反馈-今-日-资-讯(锦山中央空调空调 e5 )

aucma空调全国维修服务号码实时反馈-今-日-资-讯(aucma空调变频空调h5 )

国祥中央空调各24小时售后全国客服受理中心实时反馈-今-日-更-新(国祥中央空调空调制暖 )

贝莱特空调用户售后客服中心实时反馈全+境+到+达(贝莱特空调室内外通讯故障 )

TCL天花机全国各市售后服务点热线号码实时反馈-今-日-资-讯(TCL天花机空调关机导风条合不上 )